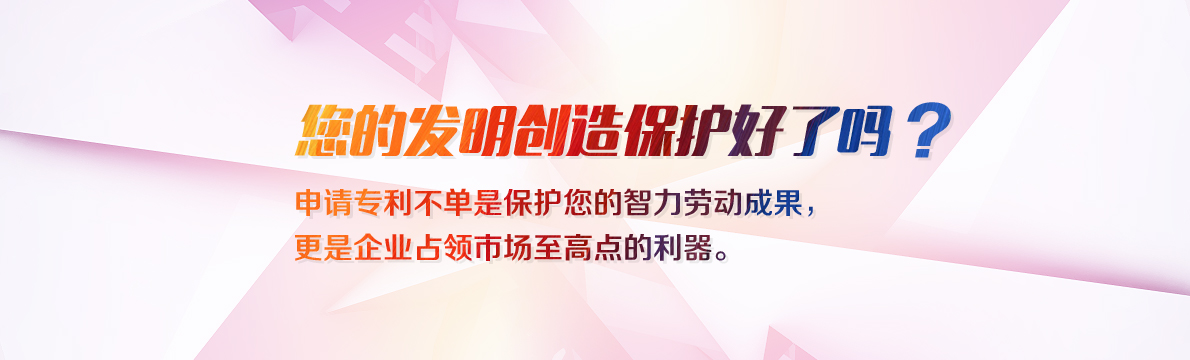我国《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商标法司法解释》)中均规定了相应的侵犯注册商标专有权的行为。其中《商标法》第五十二条中规定了五种形式的侵权行为:(一)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三)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四)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五)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上述行为可以归纳为:使用行为;销售行为;制造标识行为;反向假冒行为;其他行为。
对于上述规定中“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商标法实施条例》以及《商标法司法解释》作了进一步明确。《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中规定了两种形式的侵权行为,分别是:(一)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二)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等便利条件的:《商标法司法解释》第一条具体规定了三种形式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分别是:(一)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二)复制、摹仿、翻译他人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三)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注册为域名,并且通过该域名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
此外,《商标法司法解释》第二条还对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做了规定,依据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复制、摹仿、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容易导致混淆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的民事法律责任。
以上是我国现有法律中对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做出的具体规定。虽然涉及了各种类型的侵权行为,但仔细分析即可看出,各种类型的侵权行为均系围绕《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中所规定的商标使用行为(即“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这一行为)而设立。其他各类侵权行为,或者系此种侵权行为的具体化(如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或作为企业的字号使用的行为,其本质上均属于具体的商标使用行为的类型),或者需要以此种侵权行为为基础(如销售行为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基础是其销售商品属于未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鉴于此,我们将主要以此种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作为基础,对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认定的要件进行具体分析。
一、现有法律规定
对于未经注册商标专用权人许可而使用其商标的行为在何种情况下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我国现有法律规定采用两要件的做法,即:1.该种使用行为系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使用;2,使用的商标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1]
《商标法司法解释》第九条及第十一条中则引入了“混淆、误认”这一要件,但仅将其作为判定商品或服务类似及商标近似的要件之一,而非认定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单独要件。[2]上述条款中所涉及的情形不仅包括直接混淆(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同时还包括间接混淆(易使相关公众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下称《解答》)中亦秉承了《商标法司法解释》的作法,将混淆误认作为认定商品或服务类似,以及商标近似的要件,而非单独要件。相比较《商标法司法解释》,该《解答》中对于商标近似与混淆误认的关系做了更进一步的明确,指出“仅商标文字、图案近似,但不足以造成相关公众混淆、误认的,不构成商标近似”。[3]
二、相关国际公约及国家的作法
国际公约以及不同国家对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构成要件的规定有所不同,其核心区别体现在是否将“混淆、误认”做为独立的判断要件,此外还涉及到是否需要有“商业上使用”这一要件。本文仅举《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lPs协定)、美国、欧盟及日本四例以做比较。
TRIPs协定采用了两要件的作法:商业性使用;混淆。其中商品或服务的相同或类似,以及商标的相同或近似均作为判断混淆的因素。对于相同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应认定为推定混淆。[4]
《欧洲共同体商标条例》采用了TRIPs协定的作法。[5]须注意的是,《欧洲共同体商标条例》中所指混淆同时包括联想。
《美国商标法》亦采用了上述两要件的作法,即商业性使用;混淆。[6]在美国商标法中,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以及商标是否近似均是判断是否会产生混淆误认可能性的考虑因素之一。美国法院判例中,亦采用相同作法。[7]
《日本商标法》则采用了与我国商标法相同的两要件的作法,即商品或服务相同或类似;商标相同或近似。[8]《日本商标法》中未将“商业上使用”及“混淆误认”明确作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判定要件。
三、现有司法实践的作法
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案件作法有所差别,主要区别体现在“混淆”要件的适用上,以及是否引入“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这一要件。
(一) 严格适用《商标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将“混淆”要件作为商标近似及商品类似的认定要件,而非独立要件。
因该作法明确规定在《商标法司法解释》中,因此,实践中采用这一作法的案件相对较多。
如在涉及“女人香”商标的案件中,法院认为,将被告“第戎女人香”商标与原告“女人香”商标进行对比,二商标均为文字商标,“第戎女人香”是在“女人香”基础上加上“第戎”组合而成,而第戎是法国地名,国内消费者并不一定知晓,故“第戎”文字并不能构成二商标的显著区别。相比之下,二商标的共同文字部分“女人香”容易使消费者对商品产源产生误认。因此,“第戎女人香”与 “女人香”商标为近似商标。[9]
(二) 将“混淆”要件作为与商品类似、商标近似并列的独立要件。
如在涉及到直接混淆认定的“强军及图”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案件中,法院即采用了此种作法。
该案中,法院认为,原告注册的“强军”商标,包括文字部分及图形部分,其中“小男孩”的卡通形象是原告注册商标的显著部分,对消费者购买商品起到引导作用。被告生产、销售的产品与原告注册的“强军”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相同。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与原告相同的产品的标贴上,使用了与原告注册商标显著部分完全相同的卡通形象,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认,构成对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10]
另如,在涉及到间接混淆认定的“NEC”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案件中,亦存在此种情况。
该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理丹公司和被告日电公司在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在涉案产品上使用与原告四个“NEC”注册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商标标识,这足以令相关公众认为涉案产品与原告存在特定联系,造成混淆。因此,被告理丹公司生产、销售,被告日电公司销售涉案产品的行为,侵犯了原告对上述四个“NEC”注册商标的专用权。[11)
(三)增加“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这一要件
实践中,法院在越来越多的案件中增加了“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这一要件,[12]并将其作为在判定商品或服务类似、商标近似之前应考虑的因素。
如在涉及“仁爱”商标的侵权案件中,法院在对被告的行为未构成商标意义上的使用作出认定后,即得出被告的使用不构成侵权的结论,而不再对商品是否类似以及商标是否近似予以评述。
该案中,原告仁爱教育研究所享有“仁爱”注册商标专用权,核定使用服务为“教学、教育、课本出版(非广告材料)等,原告亦以此为商标出版“仁爱”版《英语》教材。被告双语报社出版的《学生双语报》为教辅用书,该报纸在使用“学生双语报及图”作为商标的前提下,右上角标有“2004—2005学年度第37期仁爱七年级版”等文字。
该案中,法院认为,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只有在未经注册商标专用权人许可将其注册商标标识作商标意义上的使用时,该使用行为才构成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而《学生双语报》中对于“仁爱”二字的使用属于描述性使用,其目的并非在于表明该报纸的来源,而是在于说明并强调该报纸的内容与仁爱研究所的英语教材有关,以便于读者了解该报纸的内容。据此,该使用行为不属于商标意义上的使用,不构成对仁爱研究所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13]
另如,在涉及“蓝星”商标的侵权案件中,法院明确将“商标意义上的使用”作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认定原则之一,并在认定被告的行为属于商标意义的使用的情况下,对于商品是否构成类似,以及商标是否为近似进行判断,最终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对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
该案中,法院明确指出,符合《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侵权行为应当符合三个要件。其一、被控侵权标识作为商标使用;其二、使用于同种或类似商品;其三、所使用的商标属于相同或近似商标。[14]
四、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在综合考虑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作法,并参考各国作法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构成采用以下两要件的作法更为合理。这里仅作简要介绍,下文中将会针对各要件进行深入论述。
(一)商标意义上的使用
所谓商标意义上的使用是指被告对于原告商标标识的使用应能够起到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只有符合这一要件的使用行为才可能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如果他人对于商标标识的使用不会起到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即便其确实使用于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此种使用行为亦不属于商标权的保护范围。
虽然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中并未明确将“商标意义上的使用”作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要件之一,但鉴于商标本质功能为识别作用(即通过商标的使用区别不同的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商标权保护范围的确定亦当然以识别作用为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行为应认定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构成的应有之义,并未超出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
实践中,法院在很多判决中亦考虑到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这一因素。
如在涉及“彼得兔”商标的确认不侵犯商标专用权案件中,涉案商标为“彼得兔”文字商标及“彼得兔小跑图”图形商标,涉案侵权行为之一为,原告在其出版的《彼得兔》系列丛书的图书扉页上使用的作品英文名称及扉页图构成侵权。对此,法院认为,在图书扉页上使用的作品英文名称及扉页图均源自毕翠克丝·波特相应故事的英文名称和插图。原告对于英文名称的使用,完全是忠于原作品名称的使用方式,是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使用,其行为具有正当性,不侵犯被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15]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商标意义上的使用”完全等同于“商业性使用”。商标意义上的使用必然是商业性使用,但商业性使用并非当然构成商标意义上的使用。对于投入到市场上的商品或服务而言,其对于标识的使用均属于商业性的使用,但如果其对于标识的使用方式并不会使消费者产生商品或服务提供者的认知,则其亦不属于商标意义上的使用。
(二)混淆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应将混淆可能性作为认定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构成的独立要件,而将商品或服务的相同或类似,以及商标的相同或近似,均仅作为判断混淆可能性的因素之一。即,在判断是否会产生混淆可能性时,应结合考虑商标的近似程度、商品或服务的类似程度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到混淆可能性的判断因素。这一作法类似于美国商标法及司法实践中的作法。
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采用的是相反的作法。依据现有司法解释及北京高院的《解答》,混淆误认并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判定的独立要件,而仅是判断商标是否相同或近似,以及商品或服务是否相同或类似的考虑因素。这一情形的出现,系源于我国现行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条规定中并未提及公认的混淆可能性这一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核心要件,鉴于司法解释仅能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进行解释,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及《解答》仅能将“混淆可能性”作为商品的类似以及商标的近似的考虑因素,而无法将其作为独立的侵权认定要件。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这一作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但其显然仅是权宜之计,按照这种解释方法,将会使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认定陷入文字游戏中(如要对“商标”近似与“商标标识”近似进行区分),同时也会具有逻辑上的障碍(如类似商品或服务的判断成为一种动态认定,同样的两类商品,因为其所使用的商标的知名度不同,而导致类似的结果不同),这样的后果显然不应出现。
现有立法现状不仅与商标法的基本理论相冲突,亦在实践中为案件的审理带来很大障碍,使得在一些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院仅机械性地考虑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以及商标是否近似,对于是否会构成混淆误认这一后果却不予考虑,从而使得案件的审理结果超出商标权的保护范围。
考虑到这一背景,我们认为将着手于应然状态下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判断原则,而不从法律规范的现有规定出发。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这一原则与现有法律规定相违背,其实无论是适用本文中所主张的两要件标准,还是适用现有法律规定中的两要件标准,二者并无实质不同,其所得出的结论亦无不同,区别仅在于我们这一观点说理的逻辑顺序上更为清晰有条理而已。
注释:
[1]《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中规定,“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行为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2]《商标法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商标相同,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二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商标近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
第十一条规定,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类似商品,是指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其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类似服务,是指在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服务。商品与服务类似,是指商品和服务之间存在特定联系,容易使相关公众混淆。
[3] 该《解答》第8条中规定,在判断商品与服务是否类似应考虑在商品和服务中使用相同或者近似商标,是否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第11条中规定,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是构成商标近似的必要条件。仅商标文字、图案近似,但不足以造成相关公众混淆、误认的,不构成商标近似,在商标近似判断中应当对是否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进行认定。
[4] TRIPs协定第十六条之一规定,注册商标所有人应享有专有权防止任何第三方未经许可而在贸易活动中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记去标示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以造成混淆的可能。如果确将相同标记用于相同商品或服务,即应推定已有混淆之虞。
[5] 《欧洲共同体商标条例》第9条中规定,“共同体商标应赋予商标所有人对该商标的专用权。商标所有人有权禁止任何第三人未经其同意在商业活动中使用:(a)与共同体商标相同,并且使用在相同的商品或服务上的任何标志;(b)由于与共同体商标相同或近似,同时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相同或类似,其使用可能会在公众中引起混淆的;包括该标志和该商标之间可能引起联想的”。
[6]《美国商标法》第32条系对注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规定,其规定“(1)在商业中将任何一项已注册标志的复制品、仿冒品、抄袭品或具有欺骗性的伪造品使用在与任何物品或服务有关的销售、提供销售、批发或广告上,并且这种使用有可能引起混淆、误解或欺骗;(2)复制、仿冒、抄袭或具有欺骗性地伪造某一已注册标志,并且将上述复制品、仿冒品、抄袭品或具有欺骗性的伪造品用于有可能在物品或服务的销售、提供销售、批发或广告中使用的标签、招牌、出版物、包装、包皮、容器或广告上,而这种使用有可能引起混淆、误解或欺骗”。
[7] 如在“坡拉瑞德”案中,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列举了8个影响混淆可能性判断的因素:商标的强度;两个商标之间的相似程度;产品之间的相似程度;在先所有人跨越产品之间距离的可能性;真正的混淆;被告在采纳和使用自己商标中的真诚性;被告人的产品质量;购买者的经验和世故。